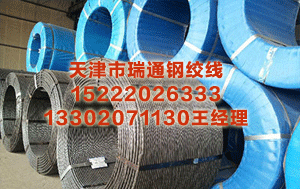茂名预应力钢绞线价格 有人偏说尧舜禅让暗藏杀机,非信血雨腥风,却不肯信真有让贤这回事?

有人盯着“尧让位于舜”这五个字茂名预应力钢绞线价格,眉头皱得能夹住竹简。
不是疑惑怎么让的,而是直接咬定:不可能。
他们认定,权力哪会拱手相送?背后一定伏尸遍野,血浸黄土,只因史官笔软,才把一场政变粉饰成道德童话。
连带着,孔融捧出那只小梨、黄香扇凉枕席、王祥卧在冰面……全被归为“古人编的感动中国”。
这股怀疑,像野火燎过竹简堆,烧得噼啪响。
可火势再猛,也得先辨风向——它从哪儿刮来的?
一拨人,信奉“人性本恶,古今皆然”。
他们看《史记》像看《甄嬛传》,读《尚书》如同翻刑侦卷宗。
尧舜之间但凡有半句客气话,立刻推断:这是话里藏刀!
舜对尧“终身慕之”,马上联想:这是麻痹老领导!
连“四岳群臣咸荐于帝”这种集体推举记录,也被拆解成:这是高层合谋,架空旧主!
另一拨人,倒不刻意阴暗,只是对上古世界全无概念。
他们拿后世王朝的龙椅、玉玺、九锡、禅位诏书去套四千多年前的部族议事棚——尺寸完全不对,硬塞进去,自然觉得榫卯崩裂,处处假。
这两种心态,一个主动染黑,一个被动失焦,最终都踩进同一个深坑:用成熟国家机器的逻辑,去丈量前国家时代的脚印。
脚印还在,只是风沙半掩。
得蹲下来,拂开积尘,看清楚那脚印的形状、深浅、朝向。
尧舜时代,根本没有“国家”这东西。
不是“小国”,不是“雏形”,是彻底没有。
现代人一听“帝王”“禅让”“继位”,脑海自动弹出紫禁城、登基大典、传国玉玺——这套符号系统,要再等两千多年才成型。
尧舜所处的社会单元,学界通称“复杂酋邦”(complex chiefdom),往上够不着早期国家门槛,往下又比平等部落多出层级。
它是什么样?
山西襄汾陶寺遗址,给了最硬的实证。
这里挖出的城址,面积280万平方米,有宫城、贵族墓葬区、手工业作坊、观象台基址。
贵族大墓里摆着鼍鼓、特磬、龙盘、玉钺,平民小墓只有几件陶器,连骨头都散乱堆放。
等级有了,但没到“君臣”那步。
最关键的一点:没有发现任何象征世袭王权的专属符号。
没有统一王陵区,没有刻着“某某之墓”的铭文棺椁,没有象征“天命所归”的青铜礼器组合。
那些玉钺,形制多样,非标准化生产;鼍鼓特磬,各墓配置不一,显然不是制度性礼器,更像是个人威望的临时加持。
陶寺的统治者,更像是一个被推举出来的“危机应对者”。
干旱来了,他组织掘井;洪水来了,他调度筑堤;外族侵扰,他协调联防。
他的权威,来自解决问题的能力,而非血统神授。
能力一旦衰退,或新人更优,交接就可能发生。
这叫“情境性领导权”(situational leadership)。
人类学在太平洋岛国、北美原住民部落观察到大量类似案例:波利尼西亚的“阿里‘i”(酋长),常由兄弟或侄子继任,前提是新人更擅航海或调解纠纷;易洛魁联盟的“ sachem”(首领),必须经氏族会议反复评议,不合格者当场撤换。
权力不是铁打的椅子,是临时借来的扁担——谁肩膀更硬,就递给谁扛。
尧舜禅让,极可能是这种机制的中原版本。
《尚书·尧典》写尧老了,“咨四岳”,问四方部族首领:我在位七十年,你们看谁接班合适?
四岳推鲧,尧试用九年,治水失败,“殛鲧于羽山”。
注意,这里不是“处死”,是流放惩戒,且仍保留其子禹的任用资格——权力未被家族垄断,失败者后代仍有机会。
再推舜,“慎徽五典,五典克从;纳于百揆,百揆时叙;宾于四门,四门穆穆;纳于大麓,烈风雷雨弗迷”。
翻译过来:让他管教化,礼法推行了;让他总百官,政事理顺了;让他接待宾客,四方和睦了;让他进深山,狂风暴雨不迷路。
全是实绩考核。
舜通过了,尧才“使舜摄政”,不是立刻交权,而是实习期。
实习八年,尧崩,舜“避尧之子丹朱于南河之南”,天下诸侯不去朝见丹朱,全跑去找舜,“然后践天子位”。
这段记载,常被解读为“舜夺权”。
可换个视角:如果丹朱真有法定继承权,诸侯为何集体背弃?
若舜真靠武力胁迫,为何要“避”?
避,说明他承认丹朱名义上的优先性,只是实践证明,没人信服丹朱能扛起扁担。
扁担,终究得挑得动的人来扛。
再看物质基础。
陶寺M22大墓,随葬玉器20件,彩绘陶器19件,漆木器残片若干。
同层平民墓,平均随葬2.3件陶器。
差距存在,但没到悬殊。
更关键的是:未发现大规模仓储遗迹。
这意味着什么?
意味着没有制度性剩余产品征收体系。
一个社会要产生世袭特权,必须先有稳定剩余,才能供养脱离生产的统治阶层,并让财富代际传递。
尧舜时代,农业靠石耜、骨耜翻土,收成看天吃饭。
山西、陕西龙山文化聚落的碳化粟粒遗存显示,单产极低,勉强糊口。
山西临汾一处遗址的窖穴,最大储粮不过三立方米——够十几人吃几个月,远不够支撑一个世袭贵族集团常年挥霍。
没有余粮,就没有“肉食者”。
《礼记·礼运》说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……货恶其弃于地也,不必藏于己;力恶其不出于身也,不必为己”。
这话未必是孔子原话,但描摹的社会状态,与考古发现高度吻合:资源紧张,必须共享;劳力宝贵,必须共担。
藏私?藏不住。
偷懒?活不下去。
在这种生存压力下,推举最强者领导,是本能,不是美德。
就像登山队遇雪崩,没人会争“按资历该谁指挥”,而是立刻喊:“绳索最熟的老张,你来!”
尧舜禅让,本质是部族版的“雪崩时刻”。
有人问:那后来怎么变成家天下了?
关键转折,在“余粮”二字。
二里头遗址一期(约公元前1750年),出现大型仓储区,探明粮窖12座,单窖容积8—12立方米。
二期起,宫城内建起连片夯土台基,贵族墓随葬青铜爵、斝,出现绿松石龙形器。
青铜礼器,是划时代的信号。
铸造一件青铜爵,需采矿、冶炼、制范、浇铸多道工序,全程脱离农业生产。
这意味着社会已能稳定供养一批专业工匠,并将稀缺铜料集中分配给少数人。
余粮出现了。
余粮一出,人性里的另一面就浮上来:谁不想把多打的粟,留给亲生骨肉?
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追述:“天子建国,诸侯立家,卿置侧室,大夫有贰宗,士有隶子弟”。
这套严密的宗法分封制,基础正是土地与人口的私有化。
但私有化不是某天突然颁布的法令。
它是一滴水,慢慢渗进陶罐裂缝。
先是工具进步:石犁换成木石复合犁,深耕成为可能;石镰换成蚌镰,收割效率提升。
山西陶寺H3405灰坑出土的碳化粟,千粒重比仰韶时期高出15%——品种在改良。
再是社会组织变化:治水需求催生跨聚落协作。
一条水渠,需几十个村子出人出力。
协调者权力自然扩大,从“临时召集人”变成“常设指挥者”。
权力一旦常设,就容易固化。
大禹治水,十三年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,表面看是公而忘私,实则是权力运行方式的质变——他需要长期驻守工地,统筹人力物资,形成固定班底。
这支班底,渐渐脱离原有氏族纽带,变成围绕“禹”个人的效忠集团。
班底要维系,得给好处。
好处从哪来?从治水新增的可耕地上来。
《国语·周语下》载:“禹疏川导滞,钟水丰物……皇天嘉之,祚以天下”。
“钟水丰物”,直白说:水利工程带来了粮食增产。
增产的粮食,一部分分给参与者,一部分留作公共储备,还有一部分……进入禹及其核心团队的私人仓廪。
私人仓廪一立,世袭冲动就压不住了。
禹传位于子启,不是某天突发奇想,是几十年资源分配实践中,早已形成“禹之团队=启之团队”的事实格局。
启能成功继位,并镇压“有扈氏不服”,靠的不是道德说服,是掌握着治水积累的物资调配权与军事动员力。
从尧舜到夏启,不是道德堕落,是生存策略随生产力升级而迭代。
就像原始人用石斧砍树,后来换青铜斧,再后来用铁斧——工具变了,砍法自然变。
没人会骂铁匠背叛了石斧精神。
禅让制消亡,同理。
有人拿“舜囚尧”“禹逼舜”当证据,说禅让全是谎言。
这类说法,最早见于《竹书纪年》战国魏国抄本,但该书原简早已散佚,今本系明代辑佚,真伪混杂。
更早的《尚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墨子》《左传》均无此类记载。
《孟子·万章上》直接驳斥:“尧舜之传,天下与贤,其心以为天下不传于贤而传于子,则是以利天下也?否!”
孟子时代距尧舜约两千年,虽有理想化成分,但若当时真有“囚禁”“流放致死”等骇人听闻之事,民间传说不可能毫无痕迹。
战国百家争鸣,连孔子都敢骂“累累若丧家之狗”,若尧舜真行篡弑,墨家、法家早拿来当反面教材,不会集体沉默。
考古更无支持。
陶寺遗址晚期(约公元前2000年),出现暴力毁墓现象:M3015大墓被捣毁,尸骨弃置,玉器砸碎。
但这发生在尧舜时代之后,且破坏者身份不明——可能是外敌入侵,也可能是内部权力重组,无法直接挂钩舜禹交接。
没有实锤,就不能当真。
宁可说“史料未载”,不可造“合理想象”。
再看那些被嘲“愚蠢”的孝行故事。
“卧冰求鲤”出自《晋书·王祥传》,时代明确在魏晋,与上古无关,本就不该混为一谈。
“扇枕温衾”“恣蚊饱血”,最早见于元代《二十四孝》,是后世道德教化文本,不能倒推古人真这么干。
但孔融让梨,有《后汉书》明载:“年四岁,与诸兄共食梨,融辄引小者。人问其故,答曰:‘小儿,法当取小者。’”
这里关键在“法当取小者”——不是天生高尚,是礼仪规范使然。
汉代贵族家庭,幼子序列本就靠后。
分食时取小份,是遵守“长幼有序”的日常实践,如同今天小孩排队不插队。
后人把它提炼成“让”,加了道德滤镜,但行为本身,只是当时礼制的自然流露。
质疑者错在把“礼制行为”等同于“道德表演”。
就像今人开会按职位排座次,没人会觉得坐末位的同事在“让座”,那只是一种秩序安排。
上古人让梨、让位,底层逻辑相同:在资源有限情境下,按某种共识规则分配,以维持群体稳定。
规则内容会变,但“需要规则”本身不变。
有人坚持:人性自私,远古必争权夺利。
可人类学观察反复证明:极端环境下,合作收益远大于争夺。
加拿大北极圈的因纽特人,猎到海豹必须全村分食,独吞者会被驱逐——冰天雪地里,你今天私藏脂肪,锚索明天暴风雪来,没人救你。
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,猎人带回肉,先交给年长女性分配,确保老弱有食——干旱频发,群体存活才有个体未来。
尧舜时代的黄河流域,洪水、旱灾、部族冲突此起彼伏。
一个总想把扁担藏自家柴房的人,早被扁担压垮了。
禅让,是生存逼出来的理性。
不是圣人多高尚,是自私的成本太高。
进入青铜时代,情况变了。
二里头遗址发现祭祀区,有集中掩埋的猪、牛、羊骨架,最多一坑37头。
这些牲畜,生前需专人饲养,死后用于仪式——说明社会已能支撑非生产性消耗。
消耗一旦常态化,特权就制度化。
夏商周的“家天下”,不是道德倒退,是社会组织复杂化的必然。
就像单细胞生物进化成多细胞,细胞开始分工:有的负责运动,有的负责消化,有的专职繁殖。
专职繁殖的细胞,自然把遗传物质传给“自己人”。
社会细胞同理。
从尧舜到夏启,不是“公”堕落成“私”,是“小共同体生存逻辑”升级为“大共同体管理逻辑”。
两种逻辑,各有其适配场景。
禅让匹配低剩余、高风险的部落联盟;世袭匹配高剩余、需稳定传承的早期国家。
硬把青铜时代的尺子,去量石器时代的脚,量出来的“畸形”,其实是量尺拿错了。
有人拿西方民主比禅让,说都是“选贤”。
这又犯了时代错位。
现代选举,基于公民权利、法律程序、政党竞争,背后是工业社会的信息处理能力与制度执行力。
尧舜推举,基于面对面熟人社会的声望评议,依赖口传记忆与仪式确认,范围不过几十个聚落。
两者内核不同:一个是制度化授权,一个是情境性托付。
但若抛开形式,看底层需求——群体总希望把权力交给最能解决问题的人——这冲动,从陶寺到华盛顿,从未改变。
只是解决方案随技术升级而迭代。
尧舜时代,解决方案是:大家围坐,评议谁最近修渠最利索、调解纠纷最公道。
今天,解决方案是:印选票、设投票站、计票公示。
工具不同,目标同源。
有人纠结禅让有无血腥。
其实不必执着“纯白”或“全黑”。
历史交接,极少绝对和平。
陶寺晚期暴力毁墓,暗示权力过渡存在冲突。
但冲突不等于篡弑。
可能是旧首领自然死亡后,新旧派系对继任者人选争执;也可能是新首领上位后,清算旧班底——这在任何时代都常见。
关键是:主流记忆是否定暴力、推崇和平交接的。
《尚书》反复强调“协和万邦”“允恭克让”,战国诸子无论哪家,提到尧舜都默认禅让为真——这说明在先秦集体记忆中,和平让渡是被广泛接受的主流叙事。
集体记忆的形成,往往基于长期实践。
若禅让真是血腥政变,很难在数百年口传中维持统一口径。
就像罗马人不会把凯撒遇刺记成“元老院温情交接”。
主流叙事能稳定传承,本身即是一种证据。
当然,不能反推“记载即事实”。
但至少说明:在那个时代,和平让贤具备现实可能性,且被社会高度认可。
可能性从哪来?
回到扁担比喻。
当扁担很重,人人知道扛不动会塌房,交接时自然少些私心杂念。
当扁担变轻,有人开始琢磨:这扁担雕花不错,不如传给儿子当传家宝——念头一起,交接就复杂了。
考古不会撒谎。
陶寺没有王陵,二里头有了;陶寺没有青铜礼器,二里头有了;陶寺仓储零散,二里头粮窖成群。
物质基础一变,上层建筑必然变。
夏朝建立,不是禹或启个人野心膨胀,是黄河流域迈过“剩余产品临界点”后的系统升级。
就像手机从功能机换智能机,不是用户突然想玩微信,是硬件支持了新应用。
硬说夏启背叛了尧舜精神,如同骂iPhone用户抛弃了诺基亚情怀——技术迭代,何来背叛?
真正该警惕的,是用后世制度反推前代。
比如拿秦汉的“禅让”比尧舜。
王莽代汉、曹丕代汉,都搞“三让而后受之”的仪式,表面学尧舜,实则军队已围宫门。
那是政治表演,不是制度实践。
把表演当原型,自然觉得原型是假的。
尧舜禅让,没有表演成分,因当时根本不存在“表演给谁看”的观众群——没有官僚系统需要安抚,没有史官需要记录,没有诸侯需要震慑。
交接在几十个聚落首领见证下完成,靠的是日常积累的威望,不是精心编排的剧本。
剧本需要舞台,前国家时代连戏台都没有。
质疑者另一个误区:把“制度”当成“个人品德”。
尧舜不是靠“无私”让位,是制度设计本就不支持长期垄断。
就像今天公司CEO退休,不是他突然高尚,是公司章程规定任期。
若章程允许终身制,多少人愿主动退?
上古没有成文章程,但生存压力形成无形章程:扛不动扁担,就得换人。
这章程,比竹简刻的更硬。
再谈历史虚无主义。
它危害不在质疑本身——历史本需质疑——而在质疑时抽掉时空坐标。
把2025年的信息过载、信任危机、职场倾轧,直接投射到公元前2300年的黄土台地上。
那时的人,没看过宫斗剧,没读过《厚黑学》,没经历信息爆炸。
他们的世界半径不过百里,信任半径更小。
一个人是否可靠,靠十年共耕一丘田、同抗一次洪来验证。
在这种环境下,声望是硬通货,作弊成本极高——你今天骗了邻族一袋粟,下次旱灾他绝不会借你水渠。
道德不是悬在空中的教条,是长期博弈筛选出的生存策略。
就像草原狼群,头狼老了自动退位,并非觉悟高,是继续逞强会拖垮整个族群,最终自己也活不成。
尧舜让位,同理。
不是圣贤多,是蠢人活不久。
有人拿出《韩非子·说疑》:“舜逼尧,禹逼舜,汤放桀,武王伐纣,此四王者,人臣弑其君者也”。
韩非这么说,是为论证“人主之患在于信人”,服务其法家集权主张。
战国策士惯用极端案例立论,如同今天自媒体标题党。
不能把辩论修辞当史实采信。
且韩非同一书里又说:“尧为人君而君其臣,舜为人臣而臣其君”,承认权力关系的特殊性——舜为臣时实际行使君权,尧为君时甘居臣位。
这恰恰说明交接是功能性的,非名义性的。
功能重于名分,正是前国家时代特点。
现代人难理解,因我们活在“名实合一”的制度里:总统名分与实权绑定,CEO头衔与决策权同步。
但上古可以“名实分离”:尧保留“帝”名号,舜掌握实权;舜巡狩四方时,禹已在中原理政。
名号是象征,实权是工具。
工具该换手时,没人纠结名号归属——只要扁担不落地。
这种务实,被后世“名教”遮蔽了。
汉代以后,儒家将禅让道德化、仪式化,变成“让德”标本。
结果真伪之争,全围着道德转:若舜真贤,为何不终身侍奉尧?若尧真爱民,为何不早传位?
问题本身已预设错误前提:把政治交接当道德考试。
其实尧舜面临的,是道工程题:如何平稳移交抗洪指挥部?
工程题的答案,不在《论语》里,在陶寺的夯土层里。
考古地层显示,陶寺中期(尧舜阶段)宫城持续扩建,晚期(夏初)出现暴力毁弃,随后二里头崛起。
这串链条暗示:权力中心转移伴随局部冲突,但整体文明未断裂,技术持续进步。
就像公司并购,总部搬迁时或有员工抗议,但生产线照常运转。
把局部摩擦放大为全面阴谋,是以偏概全。
真正的大规模血腥权力更迭,考古会有痕迹:集中杀殉、武器损伤人骨、聚落焚毁层。
殷墟有,二里岗有,陶寺晚期有一点,但尧舜对应的中期地层,干干净净。
干净不是伪造,是当时真没发生大规模暴力。
有人问:那《竹书纪年》的“舜囚尧”怎么解释?
今本《竹书纪年》系明清学者杂抄诸书拼成,其中“舜囚尧”条,最早出处是唐代《史通》引《汲冢书》,而《汲冢书》原简在西晋已残缺,唐代所见已是二手转录。
同期更可靠的《逸周书》《穆天子传》均无此说。
面对孤证,考古学原则是:存疑,不采信。
宁可说“史料未载”,不可造“合理想象”。
再谈认知偏差。
现代人习惯“权力=利益”,因我们目睹权力可兑换金钱、地位、资源。
但对尧舜而言,权力首先是责任。
陶寺观象台遗迹,显示当时需精确观测天象以定农时。
误差一天,可能误了播种,全族挨饿。
首领要统筹天文、水利、外交、祭祀,神经时刻绷紧。
M22墓主骨骸检测显示,35岁前已患严重关节炎、脊椎侧弯——长期负重劳作所致。
权力给他带来什么?更多操劳,更快衰老。
这种“苦差”,谁抢着世袭?
直到余粮出现,权力才从“苦差”变成“美差”。
转变节点,在考古上清晰可辨。
龙山时代晚期(约公元前2200—2000年),黄河流域聚落数量锐减40%,但单体规模增大——小村子合并成大聚落,应对资源压力。
合并需强力协调者,协调者权力扩大。
扩大到某一点,量变引发质变。
二里头一期突然出现青铜容器,正是质变标志:只有集中剩余产品,才能支撑高耗能手工业。
从此,“权力=资源控制权”,世袭才成为理性选择。
夏启继位,不是道德选择,是经济选择。
就像公司盈利后,创始人自然想让子女接班——不是变坏了,是条件允许了。
苛责上古人“不够无私”,如同责怪原始人“不用智能手机防汛”。
工具决定策略。
尧舜时代,最优策略是选贤;夏初,最优策略是传子。
两种策略,各自适配其时代。
硬分高下,是认知懒惰。
2024年市政道路建设:重点突破+民生提质 路网效能再升级
有人仍不甘心:难道真没一点私心?
当然有。
人性亘古未变。
但私心表达方式,受制度制约。
尧若想传丹朱,需做到两点:一、让丹朱积累足够威望;二、让各部族认可丹朱能力。
他没做到,或丹朱没做到,权力自然流向舜。
不是尧不想私传,是制度没给他强推的资本。
就像今天非家族企业CEO,想让儿子接班,也得先让他做出业绩、赢得董事会信任。
制度框架内,私心只能曲线表达。
框架一变,曲线变直线。
天津市瑞通预应力钢绞线有限公司夏朝建立后,框架变了。
二里头三期,宫城出现封闭式院落,与作坊区、祭祀区严格隔离——空间隔离是权力神圣化的第一步。
当首领住进高墙深院,日常不再与民众共同劳作,声望评议机制就失效了。
威望让位于血统。
血统需要神话支撑。
于是夏人编出“禹母吞薏苡而生禹”“启母化石启生”的传说,把血缘神圣化。
商周跟进,“玄鸟生商”“履大人迹生周”。
神话不是古人愚昧,是新制度的合法性刚需。
尧舜不需要神话,因他们的合法性来自实绩,天天在众人眼皮底下验证。
启需要神话,因他的合法性来自血统,得用超自然解释“为何是他”。
制度不同,合法性来源不同。
用神话有无,倒推禅让真假,如同用企业官网有无CEO童年照,判断公司是否家族企业——风马牛不相及。
真正该问的是:哪种制度更适配当时生产力?
答案清晰:低剩余社会,选贤制降低决策风险;高剩余社会,世袭制保障政策连续性。
没有永恒最优,只有动态适配。
现代民主选举,本质是工业信息社会的“选贤制升级版”:用投票替代口传评议,用政党纲领替代个人实绩展示,用四年任期替代终身制。
内核仍是:定期评估,择优授权。
从陶寺议事棚到现代投票站,人类一直在解决同一个问题:如何把扁担交给最合适的人?
方法变了几轮,问题没变。
执着于“尧舜是否真让位”,不如思考:什么条件下,和平交接成为群体理性选择?
答案藏在陶寺的粮窖大小、二里头的青铜作坊、殷墟的甲骨卜辞里。
不在道德鸡汤里。
也不在阴谋论的黑暗想象里。
考古铲一锹下去,黄土无言,却比万卷史书更诚实。
它说:看山是山时,山就是山。
山不会因你疑它假,就塌了;也不会因你信它真,就长出金矿。
它就在那儿,等风剥开尘,等水洗出纹,等懂它的人,蹲下来,摸一摸石头的凉意。
史料未载的,别猜。
挖出来的茂名预应力钢绞线价格,别装没看见。